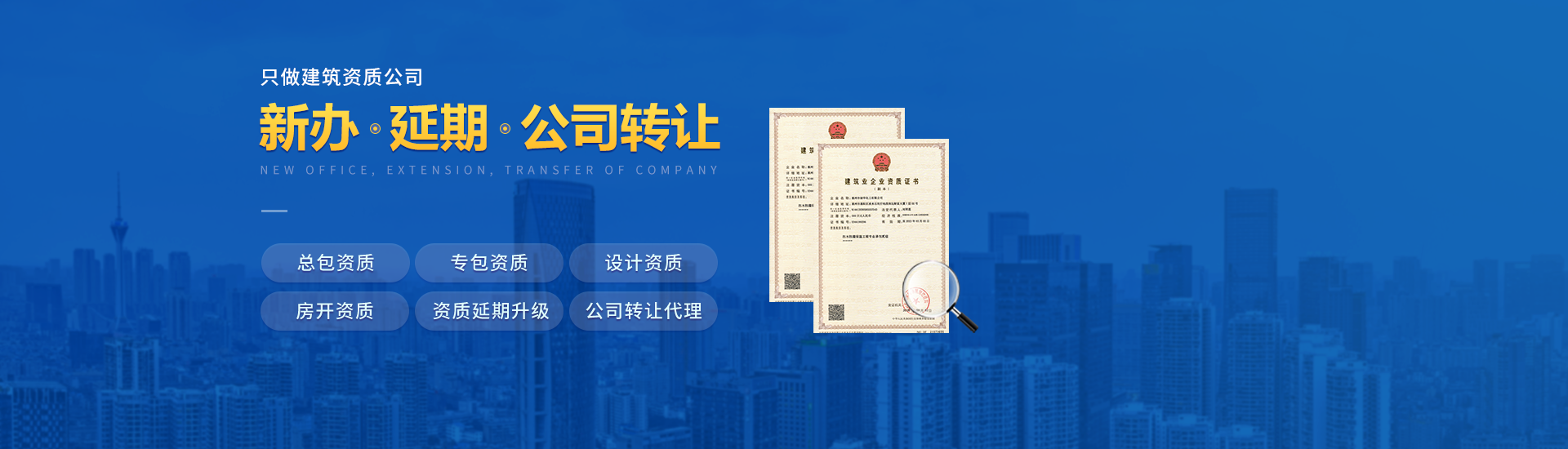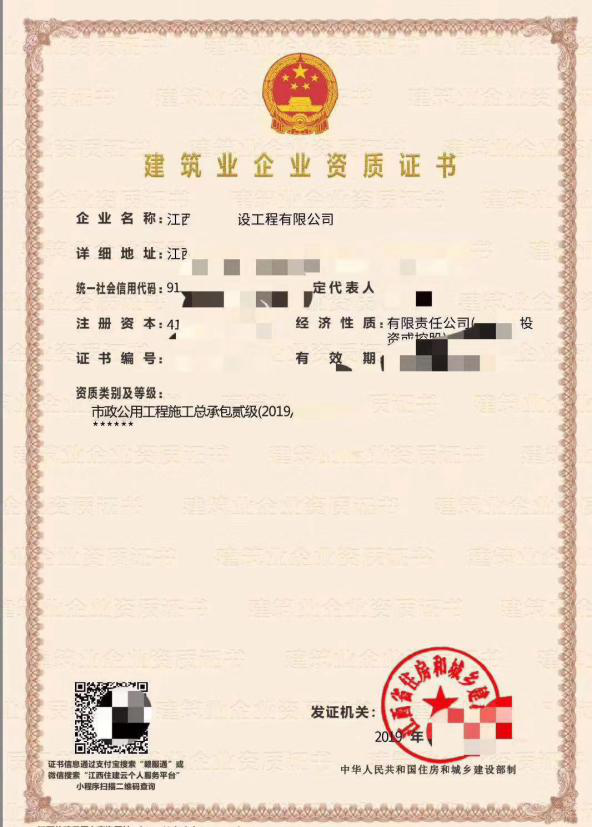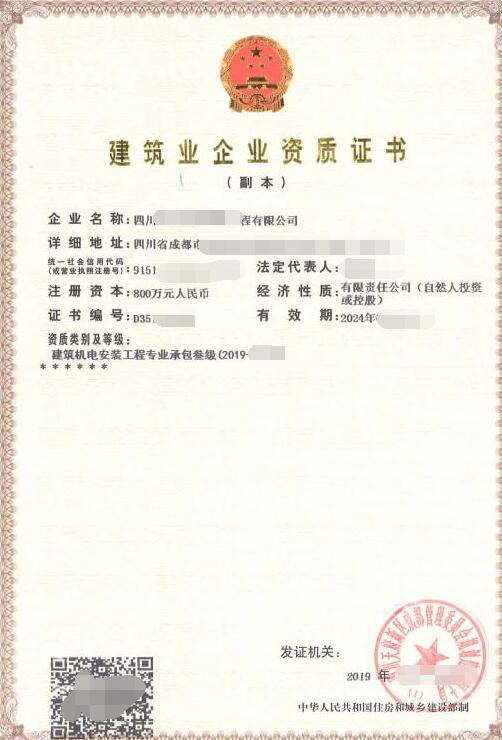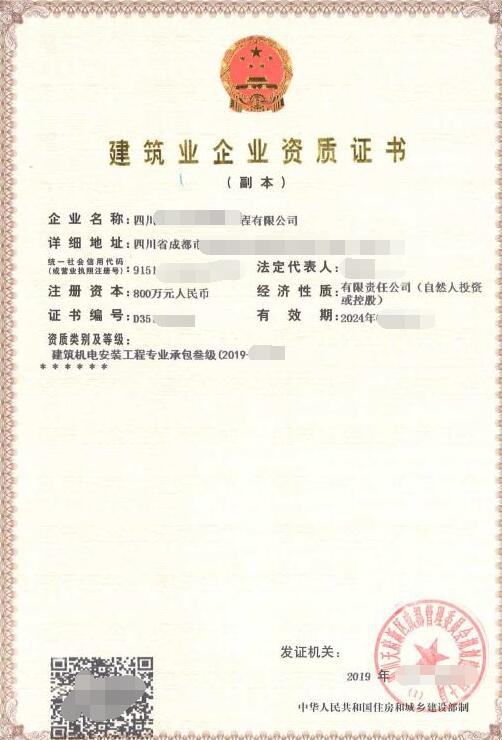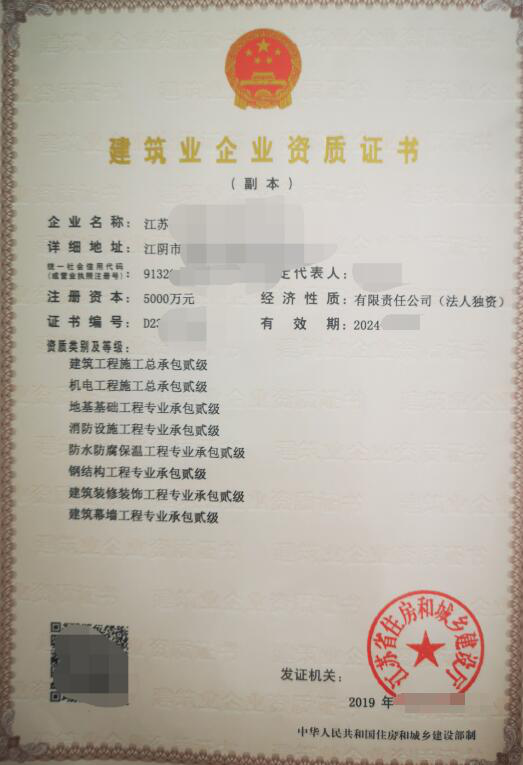當先民在青銅器上鑄下文字,歷史便已凝固其上;當玉石被打磨成器物,思想便有了載體;當泥土與火焰相遇,文明便有了形骸。這些承載著古人智慧的匠心造物,在上海博物館的展廳里構筑起立體的文明譜系——青銅器的莊嚴、玉器的溫潤、陶瓷的靈秀,共同編織著中華文明的物質記憶,也訴說著古老而璀璨的故事。
青銅為書,鑄刻文明史詩
青銅器是中國古代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志,為貴族社會崇尚禮制的特殊產物。其不僅展示了當時社會的審美風尚、鑄造技術,身上的銘文更為歷史寫下了注腳。
大克鼎是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鑄造于西周時期,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清代末年就與大盂鼎、毛公鼎并稱為“海內三寶”。整器威嚴厚重,口沿下裝飾變形獸面紋,腹部寬大的紋飾波瀾起伏而富有節奏感,蹄足上部飾有浮雕獸面。每組變形獸面紋間、足部的獸面紋鼻梁皆設寬厚的扉棱。這種夸張的獸面、扭曲的線條和深沉的鑄造工藝,構建起人神溝通的神秘場域,正所謂“器以藏禮”。
鼎腹內壁鑄銘文290字,筆畫遒勁、端莊質樸,記載了作器者“克”因其祖父輔佐周王有功而被封賞的故事,是研究西周社會政治、經濟的重要資料。周代皇室和貴族常把重要的事件鑄刻在鐘、鼎等青銅器上,這種文字被稱為“鐘鼎文”,也叫“金文”。這些鐘、鼎就是一本本記載歷史的青銅之書。
如此珍貴的文物,竟險些流失。光緒十六年(1890年),大克鼎出土于陜西省寶雞市扶風縣法門鎮,被當時的工部尚書、著名的金石學家潘祖蔭重金收藏。他去世后,大克鼎被轉移到其蘇州老家。民國初年,有美籍人士專程來華找潘氏商談求讓大鼎,出價達數百兩黃金,終被潘家回絕。抗日戰爭爆發后,潘祖蔭的孫媳潘達于請工匠打造堅固的大木箱,將大克鼎、大盂鼎等藏匿于住宅地磚之下,以躲避戰火。蘇州淪陷后,日軍多次到潘家查抄,欲搶走大克鼎,所幸始終未能找到。新中國成立后,已遷居上海的潘達于女士認為,大克鼎、大盂鼎是“國之重器”,唯有人民政府才能使兩鼎得以長期妥善保存,遂將其捐獻給國家,以供廣大人民欣賞研究。
相比于鼎的莊嚴厚重,犧尊造型更為生動活潑。犧尊是指鳥獸狀的盛酒器。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犧尊”鑄造于春秋晚期,呈水牛形,但與一般的鳥獸尊盛酒器不同,這件犧尊集盛酒與溫酒的功能于一體。牛的腹部中空,在牛頸與背脊上開有三個孔,中間一個孔套有一個鍋形器,可以取出盛酒;兩邊的孔則可以注水入腹部,用來溫酒。其結構設計超越了單純的禮器屬性,體現了實用性與藝術性的完美結合。
它的頭、頸、身、腿、臀部均裝飾有回旋盤繞的龍蛇紋所組成的獸面紋,構圖新穎奇特,具有很強的時代特征。造型與紋飾融合了中原禮制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的元素:水牛形態源自中原農耕文明,而頸部浮雕的虎、犀等猛獸則帶有北方草原藝術的粗獷風格,體現了多元文化的碰撞與交融。
在眾多紋飾繁麗的青銅器中,有一個“方盒子”體積不大、樣貌普通,卻被單獨陳列在一個展柜中。據介紹,它還是被禁止出國展覽的一級文物。這個“方盒子”就是“商鞅變法”的唯一一件遺物——商鞅方升。
它身上共有四處銘文,篆刻最早也是最為珍貴的一處是“商鞅銘文”,其大致意思是:“秦孝公十八年,齊國派遣了好多位卿大夫到秦國訪問。這一年冬天,十二月乙酉這一天,大良造商鞅把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的容積規定為一升。”此前史書上只是記載了統一度量衡的年份,而這里卻直接精確到哪一天。而且,通過這句銘文可以反推出當時的一尺有多長。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將商鞅方升收回并加刻了第二道銘文,也就是始皇帝詔書,上面明確寫出:詔令丞相隗狀和王綰負責統一全國度量衡的工作,全國各地,凡是存在差異的地方,都要做到明確和統一。從秦孝公時期的變法利器到秦始皇時代的帝國標準,商鞅方升以“一升量天下”的氣度,承載了中華文明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進程。
器以載道,構建精神符號
在古代中國,玉被用來溝通神靈、敬天崇祖、辟邪殮葬、祈求祥瑞,其質地溫潤、潔白、堅韌,又被賦予仁、義、智、勇、潔等高尚品德,為歷代文人墨客所推崇。
玉神人來自4000年前的石家河文化,個子不高,只有10.3厘米,全身青黃色,頭戴平冠,方臉、梭形眼、寬鼻、闊嘴,神色莊嚴肅穆。它雙手交于胸前,雙腿微屈,猶如一位史前巫師或部落首領,正在虔誠地與神溝通。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長江中游的江漢流域,因出土小型精致的玉器而備受關注。這里出土的玉人多是人首造型,但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玉神人是全身人像,海內外目前僅此一件。
相較于良渚玉器嚴謹的對稱美學,石家河玉神人更注重動態與表情的刻畫:雙腿微屈的踞坐姿態打破靜態平衡,凸目圓睜的神情賦予雕像生命張力。這種對“瞬間性”的捕捉,在史前藝術中極為罕見。其耳部環飾等細節,通過圓雕與透雕結合,在有限空間內營造出層次豐富的立體效果,展現出石家河先民對形式美感的極致追求。這種藝術突破,為后來商周時期玉器的寫實化奠定了基礎。
四靈紋玉勝是漢代玉器中兼具實用功能與神秘信仰的典型器物。在古代,“勝”是傳說中西王母的頭飾,左右各一個,中間用連桿貫穿發髻裝飾首髻。漢代人因崇拜西王母而流行戴勝。“玉勝”則為玉質的勝,其以透雕技法琢飾“四靈”紋樣,中間上部為“朱雀”,下方為龜蛇相交的“玄武”,兩端左側為“蒼龍”,右側為“白虎”。這件不足手掌大小的器物將四靈紋與勝巧妙結合,隔柱上淺刻篆書“長宜子孫,延壽萬年”八字,有辟邪厭勝、拂除不祥、追求長生等寓意。
玉勝材質與工藝非普通民眾可及,多見于貴族墓葬。可以想象,當漢代貴族女子將其插于發髻,行走間玉勝輕顫,仿佛將整個宇宙的祥瑞之氣隨身攜帶,在方寸之間完成了對“天人合一”的美學實踐與信仰表達。這種將抽象哲學轉化為具象藝術的創造力,正是漢代文明最動人的精神特質。
三螭紋玉觚是清代仿古玉器的巔峰之作。觚本為商周時期的一種青銅酒器,而這件觚是用玉仿雕而成。它的口部與底部作菱形喇叭狀,上下飾蓮瓣紋,中部鼓腹浮雕三條蟠螭,底足內陰刻“乾隆年制”四字篆書款。這種“上圓下方”的設計源自青銅器“天圓地方”的宇宙觀,但玉質的溫潤消解了青銅的獰厲,賦予器物典雅氣質。其功能也由酒器轉化為陳設器或花器,體現了清代文人對古物的審美重構——從實用禮器到藝術雅玩的升華。
乾隆帝熱衷古物收藏,命臣工編纂《西清古鑒》等圖錄,指導玉器仿古。此器嚴格參照商周青銅觚形制,但舍棄了青銅器的獰厲紋飾,代之以更符合清代審美的蟠螭與蓮瓣,實現“形古而意新”。當觀者凝視這件器物時,既能感受到青銅時代的威嚴,又能觸摸到清代宮廷的奢華,更能體會到中華玉文化跨越千年的生命力——它始終在傳承中創新、在仿古中超越。
窯火不息,淬煉泥土哲學
陶瓷是中華文明獻給世界的一份禮物。經過泥與火的淬煉,人類第一次改變原材料的物理性質,創造出來嶄新“物種”。它不僅是實用的器具,更是藝術的流動載體、文化的對話媒介。
黑陶高柄蓋罐出土于上海市青浦區福泉山遺址,是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黑陶的精品。器呈直口、廣圓肩、扁圓腹、高圈足,罐口上覆一細長的高柄蓋,高柄中間有一上下貫通的直孔,中段內弧,下部飾三道凸弦紋和鏤孔。圈足上飾三組由弧線三角形與橢圓形鏤孔組合的圖案。陶罐器表漆黑光亮,并且彩繪多道紅褐色寬帶紋。
黑陶是繼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優秀陶種,其中以細泥薄壁黑陶制作水平最高,有“黑如漆、薄如紙”的美稱。良渚黑陶采用輪制技術,胎壁厚度僅為0.5毫米~1毫米,燒成溫度約1000攝氏度,通過“熏煙滲炭”工藝使表面微孔滲入炭粒,形成漆黑光亮的效果。罐身與高柄分別制作后粘接,柄部中間設上下貫通的直孔,既增強穩定性,又具有儀式性功能。
青釉五足洗為南宋瓷器,是一件典型的哥窯傳世品。其胎厚釉潤,釉呈米黃色,釉面密布大小開片,黑色大開片與黃色小開片縱橫交織,這種特殊的開片被古人稱為“金絲鐵線”。足端和圈足處均無釉,露出深褐色胎骨。器內底心有六個支釘痕,系器內疊燒其他器物所留下的痕跡。整件器物制作規整,造型端莊典雅,為國內外收藏中罕見珍品。
哥窯是宋代五大名窯之一,也是唯一未發現窯址的名窯,在我國陶瓷史上是一大懸案。哥窯的開片紋并非人工繪制,而是燒制過程中自然形成,契合了宋代文人“天人合一”的審美追求。其釉色以粉青、米黃等素雅色調為主,摒棄唐代的華麗裝飾,強調“素面朝天”的極簡之美,與宋代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呼應,體現了士大夫階層對含蓄、內斂精神境界的追求。
長頸、溜肩、鼓腹,流暢的線條勾勒出優雅的形體,它就是粉彩蝠桃紋瓶,產自雍正景德鎮官窯,代表了整個清代粉彩的最高技藝。其胎質細膩潔白,釉面勻凈肥腴,呈半啞光質感。瓶身以粉彩繪八枚碩桃與雙蝠,桃象征長壽,蝠諧音“福”,二者結合寓意“福壽雙全”。八桃布局為雍正朝獨有(乾隆時期多繪九桃),且橄欖瓶形制上的蝠桃紋存世僅此一件,堪稱孤品。桃枝遒勁盤亙,果實飽滿圓潤,蝙蝠如粉蝶翻飛,線條流暢清新,布局疏朗典雅,洋溢著歡快喜慶的情致。花瓣與葉片通過渲染技法呈現陰陽向背,色彩過渡自然,極具立體感。
令人沒想到的是,這件稀世珍寶曾流落海外,作為臺燈的燈座使用。2002年,它出現在香港蘇富比的拍賣圖錄之中,引起了諸多收藏家的興趣,其中包括張永珍女士。張永珍女士的父親是民國時期著名文物鑒藏家張仲英,良好的家庭教育和鑒藏眼光使她深知這件器物的價值。經過一番激烈競價,最后以4150萬港幣拍得這件橄欖瓶,創造了當時清代瓷器拍賣的最高紀錄。購買此瓶以后,她立刻把它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
粉彩蝠桃紋橄欖瓶不僅是一件工藝絕倫的瓷器,更是一部濃縮的中國近代史。其從宮廷貢品到海外漂泊,再到回歸故土的傳奇經歷,映射了中華文明的堅韌與復興。如今,它靜靜陳列于上海博物館,以粉潤的釉色與靈動的紋飾,訴說著古代匠人的智慧、帝王的審美與民族的記憶,成為連接歷史與當代的文化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