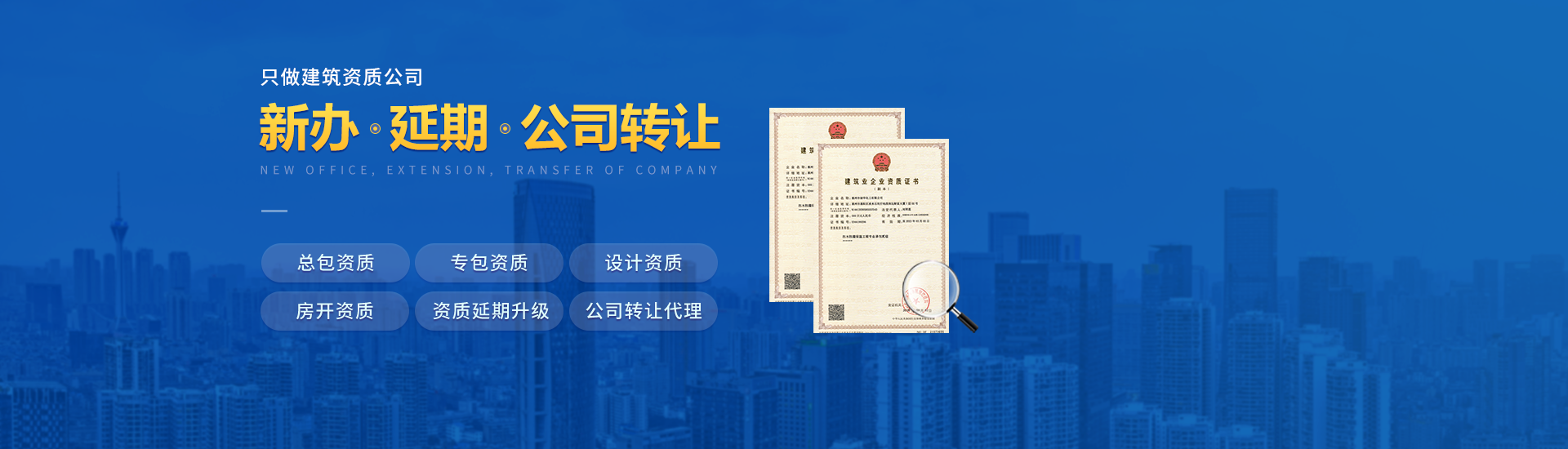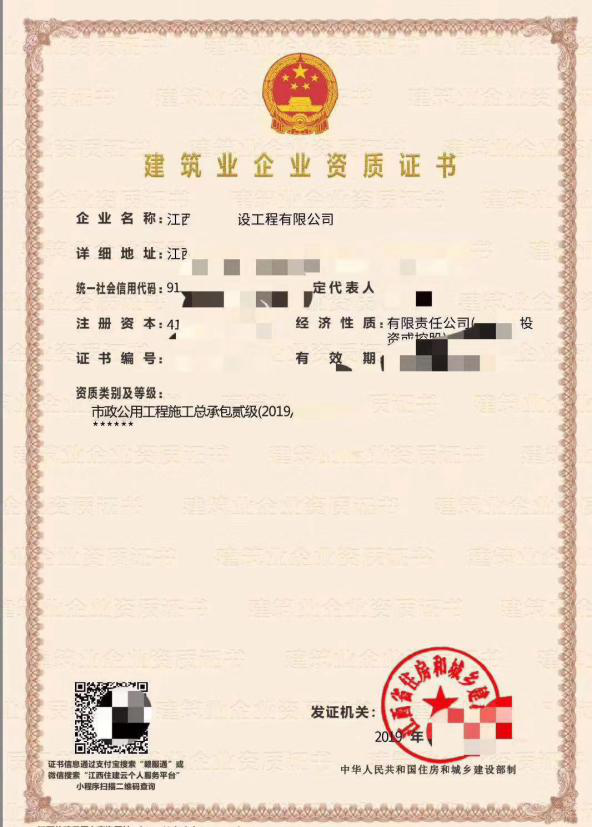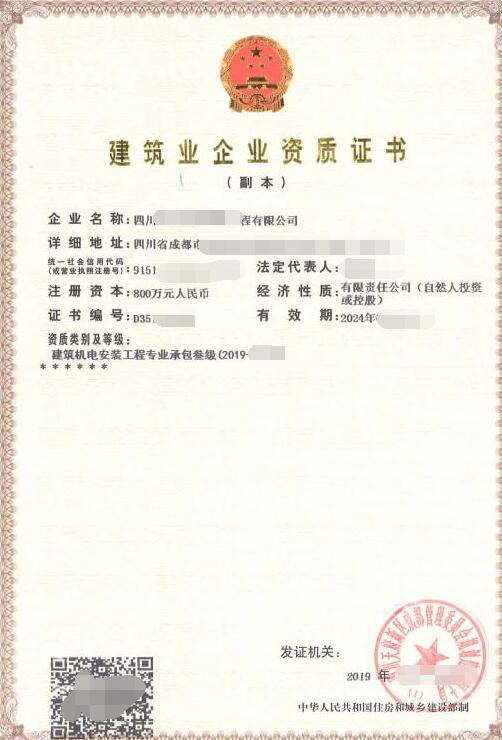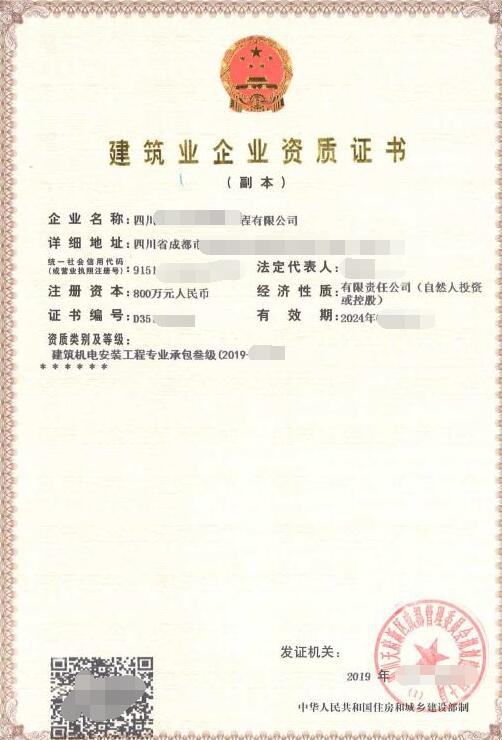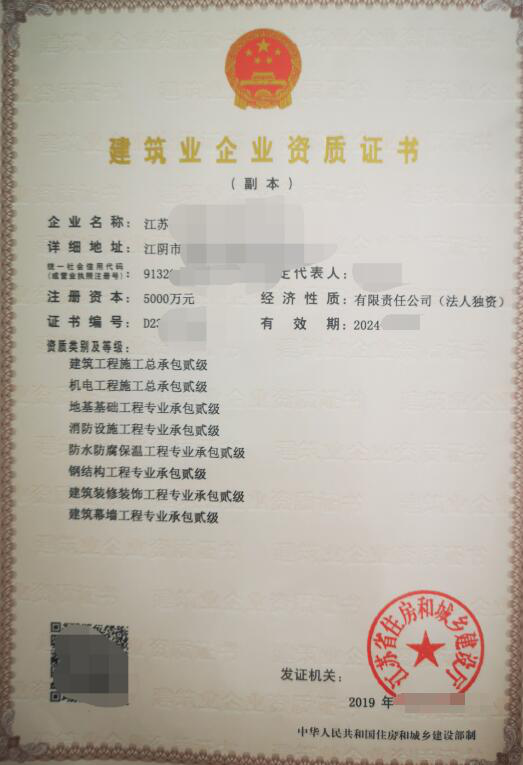一尊金翅鳥,如凝固的閃電,鎮守信仰與江河;一頂寶石冠,似冠冕上的山河,輝映權力與融合;一把舊提琴,傷痕累累,卻孕育了喚醒民族魂的驚雷……彩云之南的紅土地上,文物從來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們血脈相連,共同譜寫著多民族碰撞、交流、共生、共融的壯麗史詩。
大鵬金翅鳥——鎮守信仰與江河
來到云南省博物館,門前那尊展翅欲飛的大鵬金翅鳥雕像總是率先攫住游人的目光。它的原型,正是館藏國寶——宋代銀鎏金鑲珠金翅鳥。其通體鎏金的工藝與絕妙昂然的神姿,不僅凝固了古代工匠卓絕的匠心,更成為解碼古代云南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要物證。
初唐時期,隨著南中大姓的衰亡,滇西大理地區逐漸成為云南歷史舞臺的中心。洱海周邊興起了以“六詔”(“詔”意為“王”)為代表的地方部族。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在唐玄宗的支持下,蒙舍詔首領皮羅閣統一六詔,建立了南詔國。開國伊始,皮羅閣即親赴長安朝貢,深得唐玄宗禮遇,獲封“云南王”。南詔由此成為大唐的附屬國。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國,統治中心也在洱海周圍,基本承襲了南詔疆域,并一直與宋朝通好,保持著臣屬關系。此間,社會經濟勃興,與中原及周邊地區的交流日益深入,佛教得以廣泛弘傳,至大理國時期臻于鼎盛,被尊為國教,大理國也因此被譽為“妙香佛國”。而大鵬金翅鳥,正是這段信仰虔誠、文化交融輝煌篇章的璀璨見證。
金翅鳥原供奉于大理崇圣寺千尋塔(主塔)塔頂的木制經幢內。1978年,文物部門修復崇圣寺三塔時,發現了680余件南詔、大理國珍貴文物,其中最為精美者,便是這尊金翅鳥。它瞠目怒視,昂首展翅,蓄勢待飛,周身羽翼刻畫精細,栩栩如生。頭飾如意云形寶冠,尾羽呈火焰狀向上展開,并鑲嵌5顆水晶珠,雙足棲息于蓮座之上,喙爪鋒利,整體造型精美華麗,體態雄健圓渾,充滿勃勃生機。
但此類金翅鳥形象在云南地區并非孤例。在昆明的東寺塔、西寺塔、妙湛寺塔以及楚雄雁塔、陸良大覺寺千佛塔的塔頂四角,都裝飾有銅質貼金的“神鳥”,民間習稱為“金雞”。它們通常高約2米,頭、頸及腹部中空,其口中銜有一根兩端開孔的銅管,管內裝有金屬簧片。每逢風季,氣流穿過銅管,簧片震動,便發出悅耳鳴響。
據明代謝肇淛《滇略》記載,這些“金雞”實為佛教中的金翅鳥(梵名“迦樓羅”)。由于云南地處高原,湖泊較多,水災頻繁,民間以為是惡龍作祟,于是就想到了鎮龍治水之神金翅鳥。金翅鳥又名“大鵬金翅鳥”,是印度神話中一種性格兇猛的大鳥,位列佛教護法神“天龍八部”之一。傳說其形體巨大,展翅可達數萬里,以龍為食,正是平息水患的利器。云南先民遂奉其為“鎮水之神”,立于塔頂四周,俯瞰江河湖泊,以絕水患。
展廳中的這件銀鎏金鑲珠金翅鳥造像,集鎏金、錘揲、焊接、拼接與鑲嵌等多種絕技于一身,工匠們先分鑄出頭、翼、身、尾等部件,精雕細琢出羽毛與各類紋飾,再焊接成型。它不僅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圖騰意義,更是古代工藝的璀璨結晶。同時,它代表了云南地區當時的傳統藝術風格,其頭頂寶冠的紋飾與宋代流行玉雕飾件相似,有力印證了歷史上云南與中原的文化交流與融合。
盡管金翅鳥形象源自域外,但傳入中國后便已深深植根于中國民族文化之中。云南漢傳佛塔建筑上塑造的金翅鳥與《造像量度經》中描繪的形象大不相同,沒有人面、牛角及飾物等,而是酷似戴雞冠的“金雞”形象,這正是佛教文化融入云南民間信仰的生動寫照。
金鑲紅藍寶石冠——見證開疆戍邊與民族融合
展廳射燈掠過它的剎那,恍若將星辰與烈火凝于方寸之間,四層金瓣錯落層疊,似圣蓮綻放;冠面之上,紅寶如凝血,藍寶似深海,輝映著云南這片土地在鐵血與文明交融中淬煉出的驚心動魄之美。這便是鎮館之寶——金鑲紅藍寶石冠。它既是當之無愧的“顏值擔當”,更是云南開疆拓土、風云際會那段最重要歷史的有力見證。
1253年,忽必烈“革囊渡江”攻滅大理國,拉開了元朝經略云南的序幕。1276年,元朝在云南正式設立行中書省,并將行政中心由洱海之濱的大理遷至滇池之畔的昆明,此舉標志著“云南”成為全國統一的省級行政區劃名稱,被完全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體系。
云南行省設立后,元朝為促進當地發展,在農業、文化、交通等多個領域實施了一系列重大建設項目。其中,治理滇池水患成為關鍵舉措,這是滇池地區首次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不僅控制了滇池水患,還開辟了大量良田,之后昆明乃至全省大興屯田,昆明地區的屯田面積占全省的1/3,農業生產得到較快發展。
隨著全國南北大一統格局的形成,地區間的壁壘被打破,貫通全國的驛站制度得以建立。與政治統一相呼應,儒家思想與文化對邊疆云南的吸引力日益增強。史載,元朝統一后云南“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社會風貌煥然一新。大量中原人口因仕宦、戍邊、屯墾、貿易等原因進入云南,他們與當地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開發邊疆,極大地促進了云南地區經濟與文化的繁榮發展。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調集30萬大軍,以傅友德為統帥,藍玉、沐英為副帥,南征云貴。平定云貴后,為穩固中央對西南邊疆的統治,特命沐英率部留鎮云南。沐英去世后被追封為黔寧王,其家族世襲“黔國公”爵位,歷經十二代持續鎮守云南,直至明朝滅亡,為維護邊疆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沐氏家族也因此成為明朝最顯赫的勛貴世家之一。鎮館之寶金鑲紅藍寶石冠,便出土自沐英六世孫——沐崧之妻徐氏墓。
此金冠呈半球形,由四層形似蓮花瓣的薄金片累疊而成。冠面鑲嵌逾50顆紅、藍、綠、白等名貴寶石,色彩艷麗,與黃金交相輝映,璀璨富麗。冠兩側各有兩個小孔,以四支金簪穿入固定于發髻。其精湛的制作工藝融合了錘揲、鏨刻、鏤空、鑲嵌及焊接等多重技法,盡顯王侯器物的極致華貴。
金鑲紅藍寶石冠精湛工藝的背后,實則是明代大規模移民帶來的技術火種。為了維持明朝對云貴高原的統治,明朝實行了駐屯政策,幾十萬江南軍民攜農耕技術、手工業技藝等中原文明成果,在彩云之南扎根屯墾。此后持續的移民潮,形成了漢族人口占主體的多民族融合社會,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有了“云南人”這一共同身份。
清朝沿襲明朝制度,在云南設承宣布政使司作為省級行政機構。至雍正年間,清廷強力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廢除世襲土司,代之以中央直接任命的流官。這一根本性變革系統性地強化了中央對云貴地區的行政管控,為后續大規模外來移民的進入與深入開發創造了重要條件,并對云南社會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清代持續的經濟社會變革,深刻塑造了云南“大雜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雛形。作為中國民族種類最多的省份,20余個民族在這片土地上共生共榮,共同書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壯麗史詩,這不僅是云南最顯著的文化標識,更成為一部漢文化與邊疆民族文化交融共生、互鑒發展的立體教科書。
聶耳小提琴——奏響民族解放最強音
在云南省博物館“百年風云”展廳中,展示著一把傷痕累累的小提琴。琴身油漆斑駁,邊緣磨損,琴弓的馬尾毛已分岔斷裂,腮托卻固執地停在左下角,仿佛仍在等待主人將琴托回頦下。小提琴看似平平無奇,卻曾孕育了中華民族最激昂的旋律——它的主人就是人民音樂家聶耳。
時間的指針指向19世紀,內憂外患中,中華民族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局。云南雖地處中國西南邊陲,卻在中國近現代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關頭屢屢顯露引人注目的鋒芒。從重九起義的槍聲到護國討袁的義旗,從滇西抗戰的鐵血到“一二·一”運動的吶喊,這片紅土地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反帝反封建的重要發端。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中,聶耳,這位音樂戰士,開始用旋律作為武器。
1930年,19歲的聶耳懷揣音樂夢想,只身從故鄉云南奔赴上海。一次偶然的機會,困頓中的聶耳賺到了一筆100元的“巨款”,他一半匯給母親,一半買了把二手小提琴。從此,這把琴成了他最親密的“戰友”。他曾在日記里寫道:“若沒有旁的事來煩擾,我是會不吃飯、不睡覺,不分早晚地練習下去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序幕,“不作亡國奴”的吼聲喚起了全國人民高昂的愛國熱忱。1934年春,劇作家田漢決意創作一部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電影劇本——《風云兒女》。然而,在他剛完成一個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題歌的歌詞時,就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與此同時,身為左派活躍分子的聶耳也成了特務追捕的目標。為了安全起見,黨組織決定將聶耳轉移至日本。臨行前夕,聶耳找到夏衍,主動要求為電影《風云兒女》譜寫主題曲。
1935年4月18日,聶耳抵達東京。就在這異國的寓所里,他懷抱那把從上海舊貨市場購得的小提琴,傾注全部熱血與赤誠,在短短半個月內,就完成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最終定稿,他立刻將定稿曲譜寄回上海電通影片公司。隨著影片《風云兒女》公映,《義勇軍進行曲》很快傳遍神州大地,成為家喻戶曉的抗戰歌曲。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譽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之際,在盟軍凱旋的曲目中,《義勇軍進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然而,天妒英才。1935年7月,聶耳在日本神奈川縣海濱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年僅23歲。同年8月底,摯友張鶴(張天虛)與同鄉鄭子平將聶耳的骨灰和小提琴、日記等遺物從日本帶回上海。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際,聶耳被安葬在了昆明西山之下,《義勇軍進行曲》則繼續鼓舞著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
1949年,當新中國如朝陽噴薄而出,《義勇軍進行曲》被莊嚴地確定為國歌。開國大典上,它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的蒼穹下恢宏奏響。這份選擇,飽含歷史的深意:《義勇軍進行曲》是十余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革命斗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具有歷史意義。采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建立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
20世紀50年代,聶耳的母親彭寂寬、兩位哥哥及好友將包括小提琴在內的聶耳的個人用品、作品手稿、日記、書信等近5000件遺物捐贈給了云南省博物館,讓后人得以永遠追思這位偉大的人民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