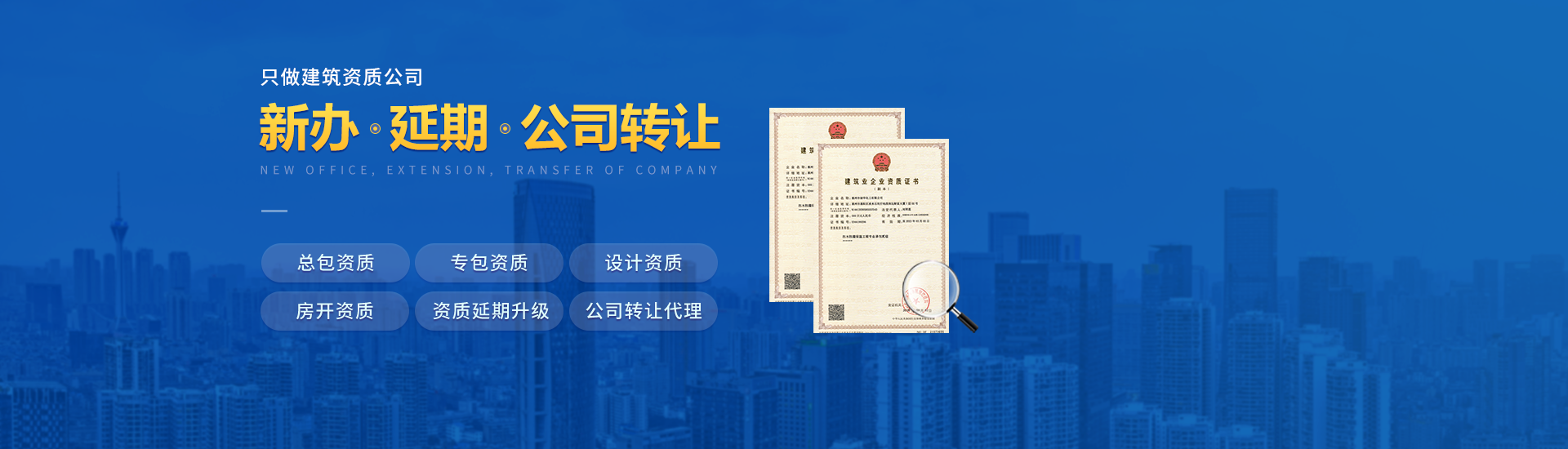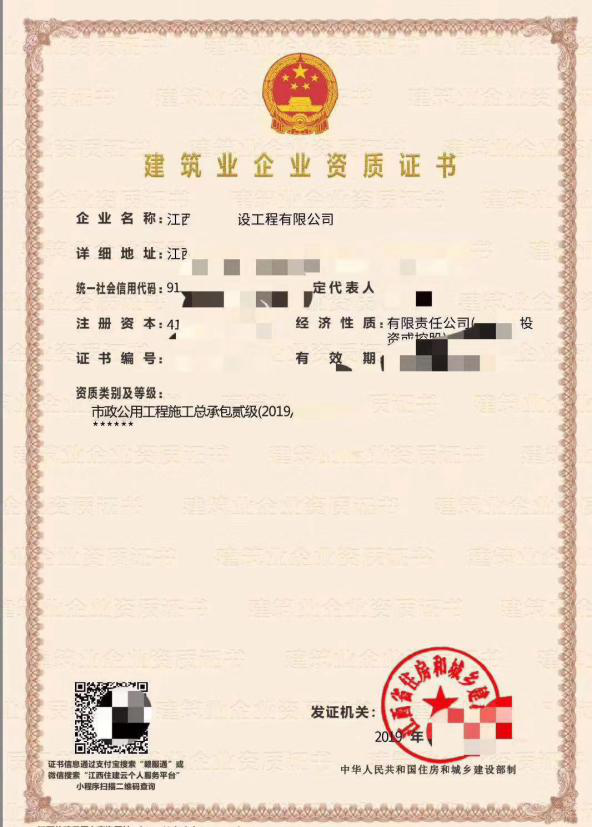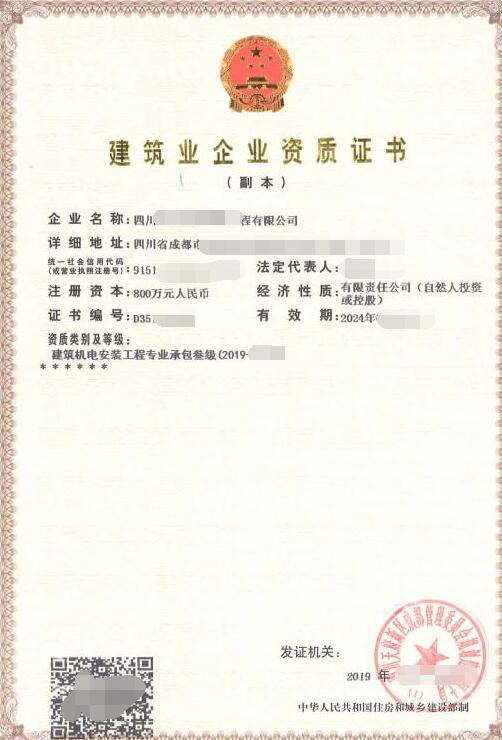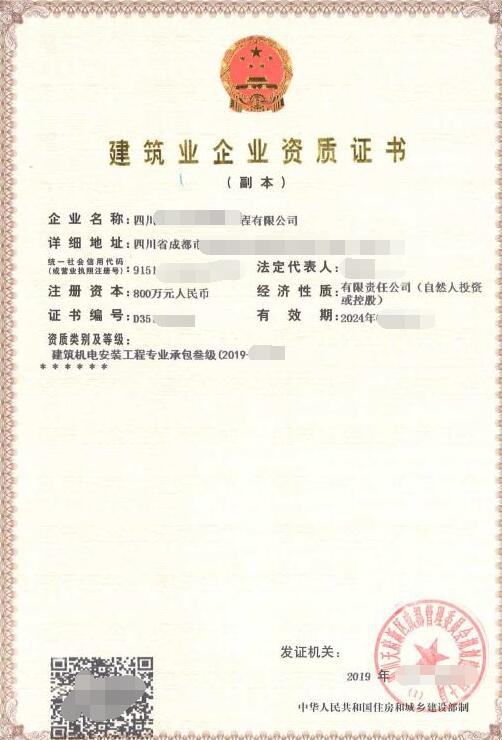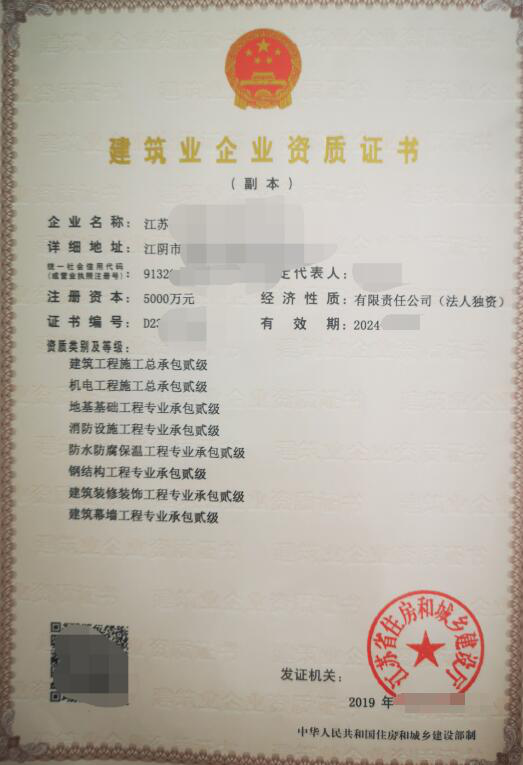八閩大地,枕山面海,文明悠悠。福建雖居東南一隅,但在文明進程中,與中原文化始終如江河與支流般血脈相連,在遷徙與融合中續寫著中華文明的多元篇章。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對當地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傾注了巨大心力,留下了豐富的、寶貴的思想和實踐財富,激勵著福建人民像愛惜生命一樣守護好八閩文化的“根”與“魂”。
福建博物院保護收藏了大量當地出土的珍貴文物,如同一位沉默的時光守護者,將八閩大地的文明密碼悉心封存。當參觀者的目光拂過展柜,仿佛能聽見文物背后閩地山海的低語,看見古港碼頭的帆影重重,觸摸到這片土地上文明生長的脈絡肌理。
潮起東南——“湖—階—館”的三重敘事
大夢山麓凝翠,西湖之畔含煙,福建博物院隱匿于園林深境。它三面環水,綠蔭合圍,南側有福州西湖公園靜臥于湖心,碧波蕩漾,厚重的文脈順著水紋靜靜流淌,共同構成一幅文景交融的和諧畫面。福建博物院建筑設計師、中國科學院院士齊康曾表示,博物院選址臨近西湖一側,湖畔粗大的榕樹郁郁蔥蔥,林水相映成趣。設計方案摒棄追求巨大、雄偉的氣魄,而選擇融于自然園林,彰顯生態特點。他在設計中融入了福建古代建筑風格和閩南石文化,讓建筑整體獨具海洋文化特色。
館區占地面積90畝,建筑面積3.6萬平方米,建筑群由西南向東北方向延展,陳列館、積翠園藝術館、自然館等依次展開,形態錯落有致,空間層次豐富。陳列館幾字形屋頂引人矚目,這種形態與福州傳統民居的馬鞍墻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建筑師只保留了其舒展的輪廓線,去除了繁復的灰塑裝飾,將原本垂直于屋脊的“馬鞍”形態轉化為水平向的波浪式起伏,形成更具現代感的幾何體塊。這種抽象處理既保留了地域建筑的識別性,又與西湖岸線形成視覺對話,使建筑在自然環境中顯得輕盈靈動。
幾字形屋頂之下,一面寬大的石階梯從二樓的展館入口直鋪下來,將西湖公園的自然景觀與博物館的文化空間串聯成“湖—階—館”的三重敘事。游客拾級而上,視線從水平向的西湖水面逐漸抬升至垂直向的建筑主體,形成“自然沉浸—文化登臨”的心理轉換。陳列館前的廣場,以入口為圓心,向四周放射出水波紋鋪裝帶,形成“潮起東南”的動態視覺效果,直接呼應福建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歷史地位。
廣場上的圖騰柱是設計中的點睛之筆。它總高40米,直徑約6米,頂部由三條癸龍狀造型頂起一個直徑近5米的大圓球。圓球內為鋼架,外包鈦金板,呈銀灰色。3米高的三條癸龍也是用不銹鋼板焊接而成的,圓柱外掛灰白色花崗巖,柱身采用陰刻凹槽,增加了垂直感。蛇與龍形態相似,又被稱作“小龍”,圖騰柱是對福建地域文化中蛇圖騰崇拜的具象表達。圓柱插入水池中,垂直形態強化了建筑的儀式感,倒影與西湖交相輝映,更增添了幾分壯麗。
自然館整體呈圓柱形,外墻為土黃色,與福建土樓的造型相似,呈現出樸實、厚重的質感,給人一種穩定、團結的視覺感受。內部空間采用了環形布局,各個展廳如同土樓的房間一樣,沿著環形通道依次排列,使觀眾在參觀過程中能夠自然地形成一條流暢的參觀路線。中央庭院則作為整個自然館的核心空間,起到了采光、通風和空間組織的作用,同時也為觀眾提供了一個休息和交流的場所。
別具匠心的建筑設計,讓規模巨大的體量“消隱”于湖光山色中,觀眾在游覽中不僅能感受到山水環繞的詩意,也會對當地文化產生更為深刻的理解。
閩人之源——守護人類早期文明
北有周口店,南有萬壽巖。萬壽巖遺址是迄今為止福建境內發現時代最早的舊石器時代洞穴類型居住遺址,把古人類在福建活動的歷史提前到20萬年前。遺址跨越了舊石器時代早、中、晚三個階段和多個時期,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哺乳動物化石和少量骨角器。其中發現的距今4萬年前、120平方米的人工石鋪地面,被稱為人類最早的“室內裝修”。
然而,這個被譽為“閩人之源”的萬壽巖,卻險些毀于炸藥包下。那時,萬壽巖早已被三明鋼鐵廠買下開采權。根據企業產能,當地的石灰石可供持續開采100年,是名副其實的“富礦”。一邊是巨額經濟效益,一邊是“幾顆哺乳動物化石”,萬壽巖何去何從?經過深入發掘,考古專家認為這個遺址非常重要。于是,有關部門向福建省政府提交了《關于三明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保護有關情況的緊急匯報》。
2000年1月1日,時任福建省代省長的習近平作出批示,一錘定音:“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作為不可再生的珍貴文物資源,不僅屬于我們,也屬于后代子孫,任何個人和單位都不能為了謀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壞全社會和后代的利益。”2000年1月25日,習近平又在福建省人大常委會《關于依法保護三明萬壽巖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的意見》上作出親筆批示:“省政府高度重視三明古代遺址保護,已于去年底專題協調,做過初步保護安排。請省文化廳進一步提出全面保護規劃和意見。”在福建博物院展廳,萬壽巖遺址出土的文物旁,展示了習近平總書記批示的復印件,教育激勵著人們一定要守住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
曇石山遺址是我國東南地區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之一,也是福建古文化的搖籃和先秦閩族的發源地。這里出土了包括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貝器、陶器、玉器和原始瓷器在內的種類豐富、數量可觀的文化遺物,具有很高的考古研究價值。灰陶塔式壺就出土于這里。它通高28.6厘米,造型特殊,上部為尖塔形狀,下部呈壺形,內部為空,風格和曇石山遺址其他器物迥然不同,顯得格外神秘。由于該器型在目前國內考古中尚屬首次發現,缺少旁證且相關研究資料不足,因此其具體用途眾說紛紜,難以定論。
有一種說法認為,它是一種燈,因為日本長野縣繩文時代遺址中曾發現很多類似陶器,有的里面還殘留有燈芯草,但日本的繩文時代較曇石山遺址晚了一兩千年,因此這件陶器也被譽為“東方神燈”“中華第一燈”。也有專家認為它是一種法器、“魂瓶”,無論是哪種用途,灰陶塔式壺都寄托了福建先民直面死亡,祈求“靈魂不朽”,并為后人積福累德的樸素愿望。
劍與鐃——閩越青銅之光
夏商周時期,中原地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青銅文明,而福建的青銅考古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片空白。2005年福建浦城縣管九村土墩墓群的發掘,不僅為我們解開了福建青銅時代的神秘面紗,也打破了“福建先秦無史”的傳統認知。該墓群的年代約在夏商、西周至春秋階段,出土了青銅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共200多件,其中青銅器有72件,器形豐富,包括劍、戈、矛、箭鏃、杯等,是福建地區一次性出土青銅器最多的考古發現,入選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西周青銅雙耳杯是出土文物中的典型代表。它整體造型較為奇特,杯身兩面裝飾有不同的獸面紋,這些獸面紋線條流暢,刻畫細膩,形態神秘,給人以威嚴、莊重之感,展現出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技藝和獨特的藝術想象力。兩側的附耳高于杯口,上面鏤空雕刻著夸張的云紋,宛如一對優美伸展的鳥羽雙翅,不僅增加了器物的立體感和層次感,還使整個青銅雙耳杯更具動感和藝術感染力,仿佛充滿了靈動的生命力。它的主人應該是酋長或部落長,說明伴隨著青銅文化的產生,當時生活在福建北部的人已經進入階級社會,貴族的生活十分奢華。
墓群出土的多把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銅劍中,有一把備受矚目。它通長34.2厘米,身寬4.7厘米,身呈墨綠色。雖然深埋地下三千多年,但出土時仍然寒光凜凜,刃部鋒利如新。劍身兩側有很寬的血槽,劍柄兩側附有鏤空耳。劍身以及劍柄都雕刻著細膩的云紋、云雷紋和竊曲紋等,線條流暢且層次分明。這把短劍工藝復雜,紋飾精美,使用材料好,代表了當時閩越先民極高的青銅鑄造工藝,應為閩越貴族所擁有。由此劍可看出越人善鑄劍,從西周時期就已初見端倪。
鎮館之寶西周云紋青銅大鐃是商周時期東南地區青銅文明的杰出代表。它出土于福建建甌市陽澤村黃科山,重100.35公斤,通高76.8厘米,腔體呈合瓦形,兩面各有圓枚18個,甬(即柄)部中空與腔體相通。通體以商周時期流行的云雷紋為主,甬上部兩面各飾獸目一對,與云雷紋組成獸面紋。鼓部中央高起處亦飾獸面紋,雙目突出,鼻梁高聳,具有威懾力。器物通體銹色翠綠,紋飾精美,造型渾厚古樸。
鐃在中原地區被用作樂器,形制像鈴鐺,但是沒有鈴鐺中間的鐸舌。演奏時,鐃口朝上,用木槌敲擊鐃口中間或兩側,能發出兩種不同的樂音,可謂“一鐃雙音”。《周禮·鼓人》中記載“以金鐃止鼓”,指的就是以金(即銅)制成的鐃敲響后,作戰的鼓聲必須立即停止,可見鐃還是停止戰鼓的信號,也是撤退的集結號。成語“鳴金收兵”中的“金”指的就是鐃。而南方的青銅大鐃則另成系統,用作祭祀之器,廣泛分布于百越之地。
西周云紋青銅大鐃既是中原禮樂文明向南方傳播的見證,也是地方文化與中原文化交融的產物,其“和而不同”的交融智慧,成為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內在動力。